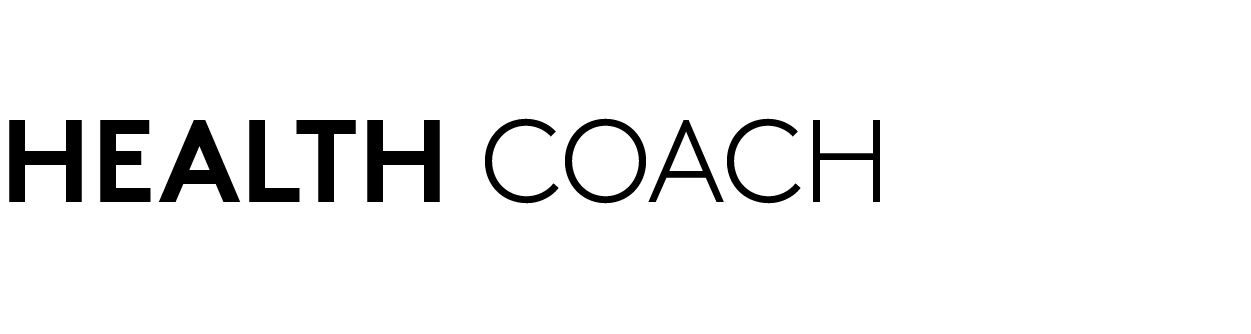在宇宙的所有颜色中,我特别喜欢两种颜色:紫色和黑色。前者是为了写作。我所有的钢笔都是紫色墨水。后者是用来穿的。我穿黑色很多 - 就像,在所有场合都不会失败。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前几天我的孩子们偷看我的衣橱并开始描述里面的物品时,我经常穿它:一件黑色夹克,一条黑色裙子,一件黑色上衣,另一件黑色夹克......
每当我遇到一位女士穿着多色服装和配饰,轻松携带她选择的款式时,我都会露出钦佩的微笑。但是,再多的尊重也不足以让我跟随她的脚步。也许一两天,我试试。我告诉自己足够了,我会照亮我的衣橱。是时候让我拥有一套与色谱中所有色调相匹配的服装了,我宣布。抓住我的疯狂虽然持续很强大,但会消失。无论是在文学节上发表演讲还是在篮球场接孩子,我都穿着黑色。
我是一个游牧民族——在智力上、精神上和身体上。从孩提时代起,我就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斯特拉斯堡、安卡拉、马德里、安曼、科隆、伊斯坦布尔、波士顿、安娜堡、图森。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一直在伦敦和伊斯坦布尔之间通勤。一天,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一位读者认出了我,问我们是否可以自拍。当我们并肩而立时,对比令人吃惊:她都是鲜艳的色彩,而我则相反。她笑着说,你不写哥特小说,但你穿得像个哥特作家!
这是一段记忆:当我决定抛开一切,独自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搬到土耳其最疯狂和最狂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时,我还是一名 22 岁的有抱负的作家。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后获得了适度的好评,我刚刚签署了第二本书的合同。同一周,我受邀在一个大型书展上发表演讲。那天早上我醒来时感到有点紧张,并决定薰衣草是今天的颜色,我认为它适合我烫过的长发,我刚刚染了最亮的姜黄色。我穿着飘逸的珍珠紫色裙子和淡紫色上衣,准时出现——但我一进入会议室就停下脚步,感到完全石化。
男作家很注意自己的外表(鞋子和腰带,金银戒指,项链),但女作家完全没有颜色。他们没有佩戴配饰,也没有化妆。小组进展顺利;讨论很热烈。结束后,一位年长的女小说家用冰冷的声音喃喃自语:亲爱的,给个建议。你说话很有口才。但如果你想被认真对待,你必须看起来更认真。
这种经历被多次重复。每当我在土耳其文学机构的陪伴下,试图了解他们的方式时,我就会听到脑后那个唠叨的声音告诉我我格格不入。我原以为土耳其的文化圈会更加平等。我错了。我明白在这个地区,男性小说家主要是小说家;没有人关心他的性别。但女性小说家首先是女性,然后才是作家。我开始注意到有多少女性学者、记者、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试图通过系统地女性化来应对这堵玻璃墙。这是他们在父权制和性别歧视中生存的策略。然后它变成了我的。
慢慢地,我改变了我的风格。我让理发师把我头发上的红色去掉。我丢弃了衣柜里的蓝色、绿色和橙色。然后是黑色戒指、黑色项链和黑色牛仔裤。我不是孔雀。我会是一只乌鸦。黑色为我提供了一种盔甲,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划界;它在我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划出了界限。唯一未受影响的是我的小说。 Storyland 有自己的颜色。它永远不会减少到一种阴影。
这是另一个记忆:我出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父母是土耳其人。我父亲正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就在我来之前,我妈妈从大学退学,认为爱和家庭就是她所需要的。我们的学校充满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各个民族的学生。我的父母想拯救世界,但他们的婚姻失败了,他们分道扬镳。
妈妈和我回到安卡拉,在一个保守的穆斯林社区与我的祖母一起避难。有眼睛从蕾丝窗帘后面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判断。年轻的离婚者被视为对社区的威胁。但奶奶出面干预:我女儿应该回大学。她应该有工作。我由奶奶抚养长大,我称她为安妮(母亲)。我自己的妈妈,我叫 abla(大姐姐)。
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一个内向的人。许多下午,我带着一本新小说爬上了我们的樱桃树。我会读书,吃樱桃,左右吐坑,假装可以到达远处灰暗的棕色和灰色房屋。我梦想着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一抹樱桃红。
与此同时,妈妈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性骚扰在街头随处可见。她会在她的手提包里带着大的安全别针来戳戳公交车上的性骚扰者。我记得她穿得多么端庄——裙子到脚踝,厚外套,完全没有化妆。最终她成为了一名外交官。在男性主导的外交世界中,她也继续穿着不暴露的衣服。她想看起来尽可能强壮。
今年夏天,当我回到英国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开始我的新小说时,我决定只打包一件衣服。我有一个计划。由于在一个微风习习的渔村没有理由专门生产黑色服装,我不得不购买一些杂色衣服。我的计划奏效了——一天。接下来,我乘坐出租车前往最近的商场买黑色衣服。
我穿黑色很舒服,但我不喜欢穿得太舒服——因此我有一种总是质疑自己的冲动。我意识到,尽管很不情愿,我对鲜艳色彩的抵制可能源于负面的个人经历,每一种经历都留下了微妙但顽固的影响。哦,我知道广告会告诉我什么。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做你自己!忘记其余的!但是,记忆和经历,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反应方式,难道不也是构成自我的一部分吗?
经过这么多次尝试和错误,我接受了我实际上喜欢穿黑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颜色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以应对父权制世界。我不必改变,只要它让我快乐并且仍然是个人选择。因为我不喜欢穿颜色,但喜欢有颜色,所以我找到了另一个解决方案:我让我的配饰闪闪发光——绿松石戒指、洋红色手镯、太阳光围巾。我的衣服越黑,我的配饰就越疯狂。
女人的一生有很多个季节。黑色的季节,颜色的季节。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人生是一场旅程。它也是混合性——对比的混合。正如诗人哈菲兹所写,你携带着所有的成分/把你的存在变成快乐,/混合它们。
Elif Shafak 是土耳其作家、活动家和演说家。她写了10部小说,包括 爱的四十条规则 和 伊斯坦布尔的混蛋 .她最新的小说, 夏娃的三个女儿 ,将于 12 月 5 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