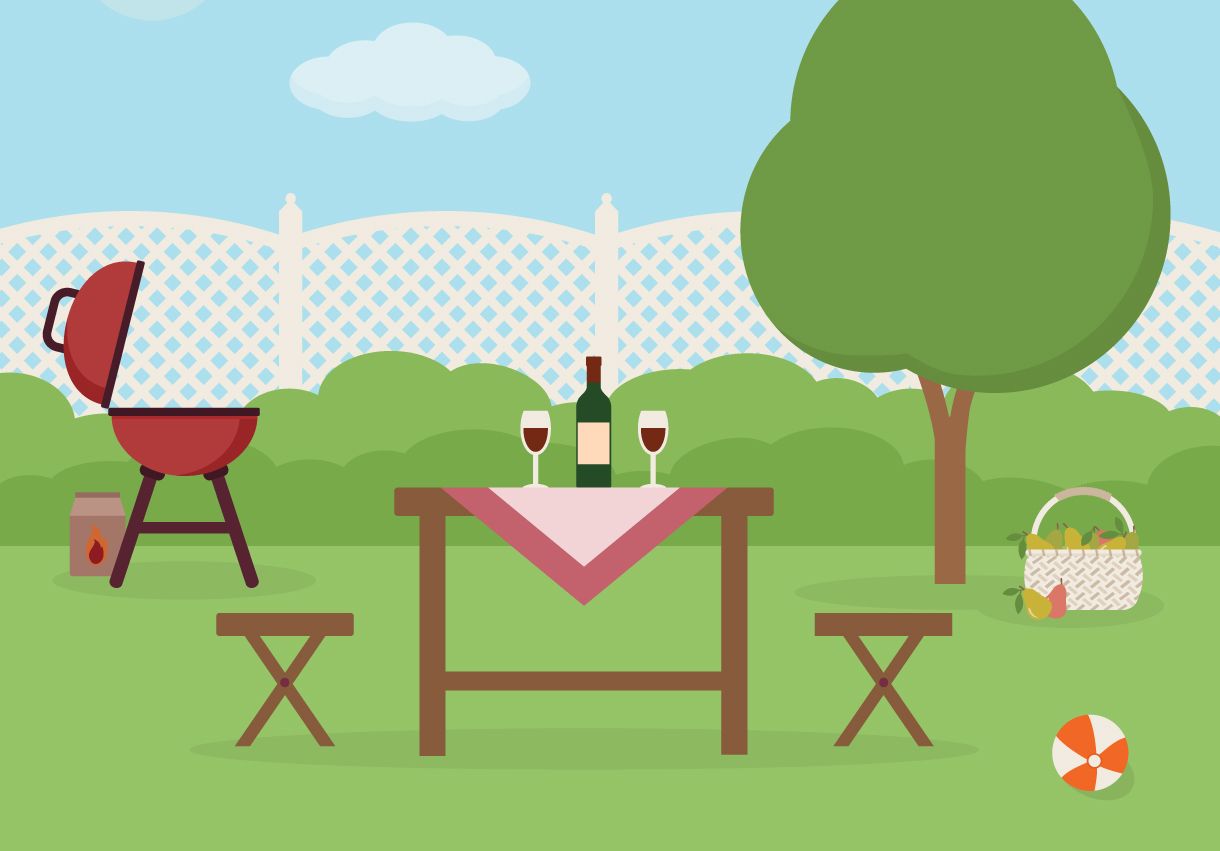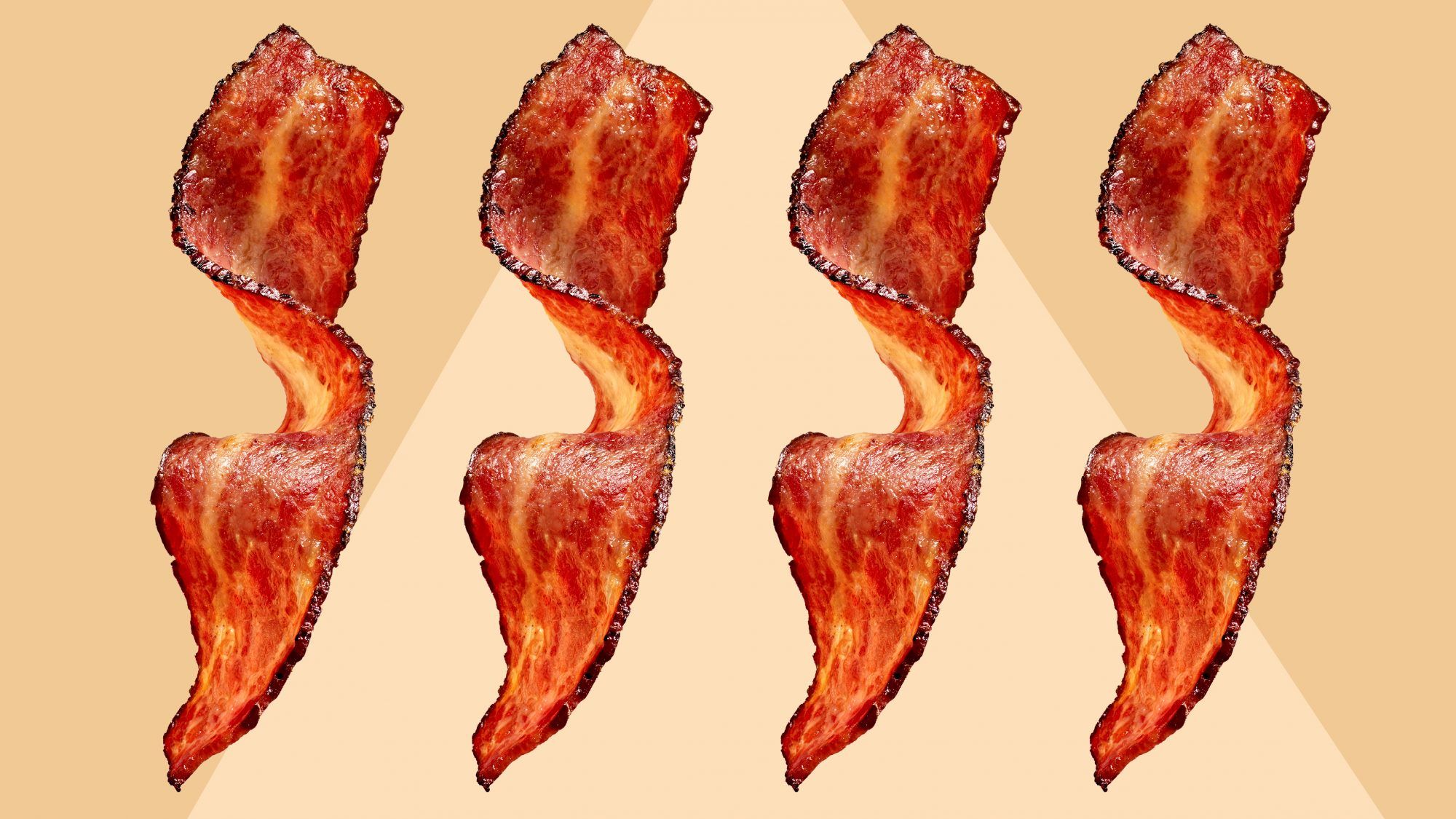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每个人——产后护士、儿科医生、哺乳顾问——都不断提醒我加入新父母小组。我理解为什么从理论上讲,小组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从我记事起,我身份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过小组成员。
尽管如此,亲密、亲密的友谊一直是我感觉被理解和联系的一部分。我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单身,以至于我和我的朋友做了很多夫妻经常做的事情。我们通宵聊天。我们在康涅狄格州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开车。我们进行了长途旅行,并在大学假期期间参观了彼此的童年家园。
我的一位越野队友 Emily 和我曾经去芝加哥最高档的餐厅之一品尝固定甜点。这是人们约会的地方,当我打电话预订两人时,主人一定认为我们会是一对穿着考究的情侣庆祝特殊场合——而不是两个 20 岁的年轻人将钱包和交通卡装在免费的大学手提袋中。女主人让我们坐下,急忙为我们的桌子拿了第二个钱包凳。看到我们软软的、脏兮兮的手提袋放在配套的室内装潢上,我们笑得脸颊都疼了。
但是,当我怀上我的女儿时,Emily 在全国各地的加利福尼亚州。我的大多数其他朋友都没有孩子……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打算这样做。
很多女性成为了母亲。我永远不会考虑潜在朋友的女性:从不使用免费手提袋的女性,更不用说带它去五星级餐厅的女性,不关心书籍的女性,或者丈夫与我完全不同的女性。这正是为什么加入一个唯一共同特征是母性的团体的想法对我来说似乎如此肤浅。
但是,我很快发现,我成为母亲后改变的方式并不是肤浅的。这始于劳动。我读了怀孕的书,但没有人能让我做好准备,让我知道我会多么了解我女儿——以及我自己——在分娩期间的死亡。一旦我度过了那些小时,我就想和某人谈谈这件事。我还想和某人谈谈血腥的乳头以及我对 SIDS 的恐惧。我想看着某人的眼睛,他也开始了解新生儿最初几周的难以想象的疲劳。而且我真的不在乎这个人是否携带名牌钱包或促销手提袋。我感到与我所知道和所经历的一切都如此孤立。
我决定去妈妈组。
在会议上,我对无法与 20 位女性进行亲密交谈感到不知所措。我们坐在儿科医生办公室候诊室的一圈椅子上,我们的婴儿坐在我们的腿上或睡在汽车座椅上。女性询问有关母乳喂养的衔乳和婴儿睡衣的问题,有时另一个女性提出的问题与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非常相似,以至于我会感到泪流满面。但是,与此同时,我想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的宝宝喂奶,她是否会在回家的路上睡在车里,我是否做对了任何事情。我筋疲力尽了。我爱我女儿的方式让任何其他类型的爱或联系都显得次要。我很少回到小组,尽管我经常感到缺乏我想象中它可能给我的支持网络。
当我女儿 15 个月大时,小组中的一位女性创办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如果有一种方式让我觉得结交新朋友很自在,那就是它了。当我准备离开时,我有了第二个想法,拼命想找一个不去的借口。我参加只是因为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似乎太粗鲁了。
那天晚上,一个我之前只见过一两次的女人正在谈论她不得不出差参加葬礼时很难找到托儿服务。她附近没有家人,她发现很难信任一个陌生人带着她年幼的女儿。我知道我们彼此不太了解,我听到自己说——有点戏剧性。但是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问我。我想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女儿刚满两岁,儿子就出生了。我又回到家,精疲力竭,流血,睡眠不足,在新英格兰阴冷的仲冬有一个新生儿。我既没有体力也没有精力去考虑买杂货和做饭。但这一次,妈妈组的女性——其中一些我什至不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带来了热腾腾的家常饭菜,然后把她们留在了我们家门口。我给婴儿喂奶,而我丈夫则端出两份成人和一份幼儿大小的意大利面或扁豆汤或鸡肉馅饼。我早早就睡了,尼克把剩下的打包好第二天吃午饭。
吃一个我认识的女人自制的肉丸子,她和我一样疲惫、感动、害怕和敬畏,当然,这与享受早期友谊中长时间不间断的谈话或大笑直到我们的脸颊受伤不同。但它的持久性也不逊色。
我还在妈妈小组读书俱乐部,我们下周见面。我们做了很多我想象中的事情——我翻了个白眼——一个妈妈团体可能会做的事情。我们谈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丈夫,我们在夏天喝桃红葡萄酒。有些人没有读完这些书。但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点不同。
我在我的越野团队、我的留学计划、我的高中英语教学工作中结交了朋友。我们是记录英里的跑步者,南非的美国人,2000 名青少年建筑中的成年人。我们在团队巴士上,在克鲁格国家公园的篝火旁,在欢乐时光中巩固这些友谊的时间也被有限或表面的共同点所定义。然而,当谈到生完孩子后交朋友时,我认为母性的担忧与其他友谊的深度存在表面上的对立。我害怕古怪、好奇、独立——我一直认为是朋友必不可少的品质——与母性格格不入。
相关:如何处理剩余的红酒
交朋友很难。作为一个成年人更难,我发现,作为一个妈妈更难。我没有进行过任何冒险,也没有经历过任何转变,这使我与过去的我分开。两个女人当妈妈不是友谊的开始,就像一起出国留学不是友谊的开始。但是母性是一种共性,它为有意义的理解打开了大门,就像曾经在地球另一端的城市中的两个美国大学生一样。也许它更大。毕竟,我从南非回来,成为了一个曾经去过那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