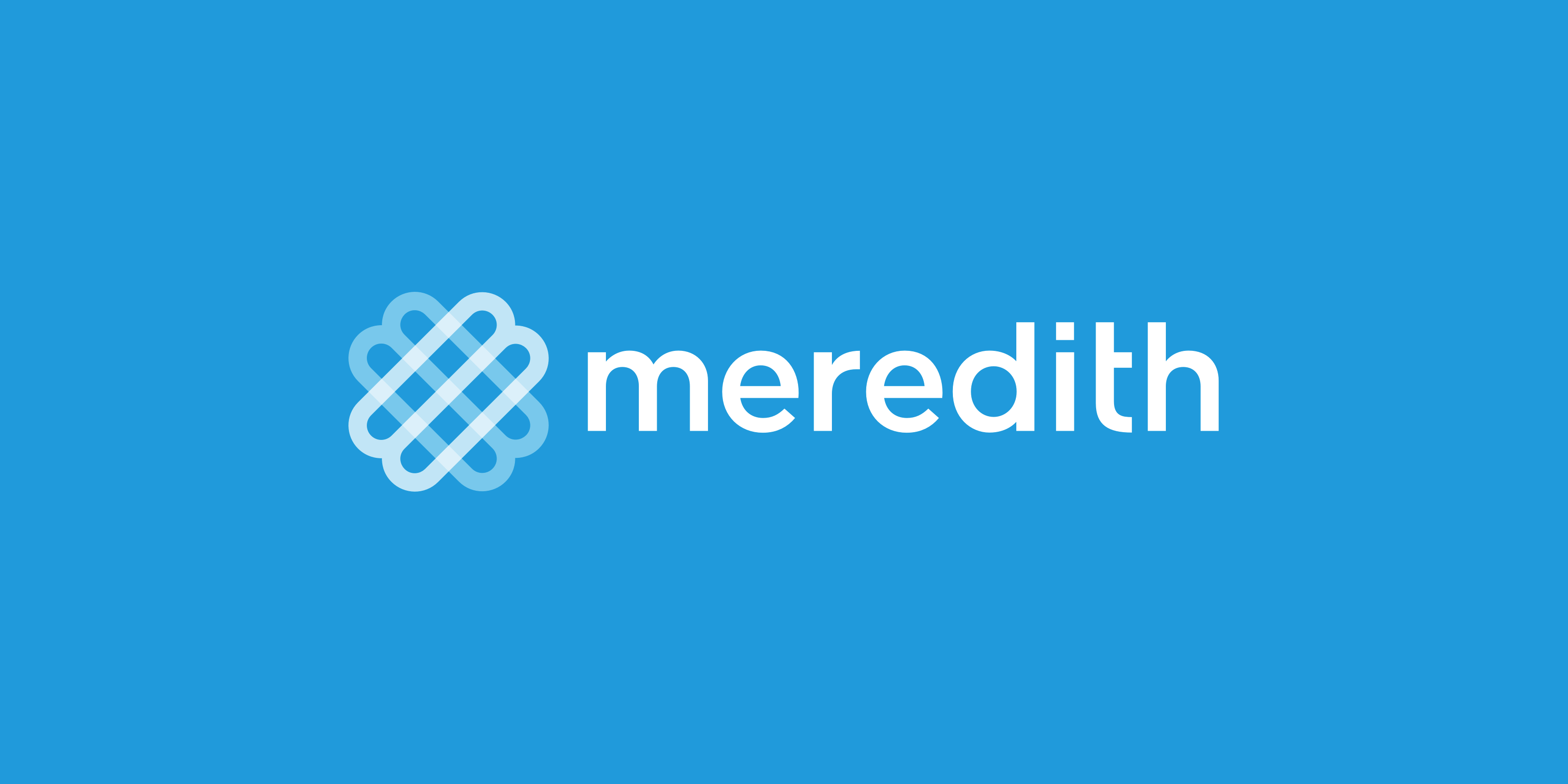让我把你介绍给我妈妈。一个长期从政的女性,一个对家庭或个人生活从不感兴趣的人,控制欲强,来时强硬。阿尔玛·菲奇有很多优点——她很有创意,善于阅读,善于表达,对世界充满好奇,而且幽默风趣——但对我来说,她是一个糟糕的对手,一个反复无常、强烈而富有想象力的孩子,渴望被理解。曾经有人问她对我的童年有什么印象。她很尴尬地承认她只记得我一直很生气。
幸运的是,我们活得足够长,看到我们的关系温暖到了亲切的休战,甚至是欣赏。她为我的写作、我对她唯一孙子的养育感到自豪,我钦佩她的精明、她的许多成就,而且常常是女性的第一。 81岁的她还在工作。
我们预期的最后一件事是痴呆症。
它始于未付账单。服药了。手机和厨房无绳之间的混乱。她在家里全天候帮助我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不想重复那场杂耍。一旦她决定搬进养老院,她就再也没有回头。那是典型的阿尔玛,从不留恋婴儿照片。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拆除这所房子。在被淹的地下室、维修、干腐、木匠、保险、三个托管,加上价值 50 年的东西之间,准备出售它被证明是我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年。但这也是我妈妈第一次让我为她做任何事。她实际上注意到了我的时间和理智方面的损失,我的书延迟。她的赞赏让我吃惊。她对别人的要求很高,却很少注意到他们的牺牲。我感到被人看到和被爱,这是我作为她的女儿 50 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
现在她离开了房子,很明显她需要做点什么。早在 50 年代,她就画过画。她喜欢她新住所的艺术课,我问她是否想要私人课程。她认为她会,所以我安排老师一对一地和她一起工作。她的自尊心开花了。有消息说阿尔玛·菲奇是一位艺术家。她找到了一个新的自己,值得骄傲,值得期待。
她安顿得很好,但失忆让她感到焦虑,有一种事情没有解决的感觉——电话无人接听,信件无人接听。我决定介入——帮助她写信,给她的老朋友打电话。我与刚刚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母亲的另一种生活。
一天下午,她吐露心声,我怎么待你之后,没想到你会这么照顾我。我以为你会回我。快乐和悲伤以同样的力量在我心中涌动。悲伤她对我的看法如此糟糕,即使是在晚年。很高兴她终于看到了我原来的样子。
到那时,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新人。不再是我的妈妈。我现在倾向于叫她阿尔玛。她甚至看起来不一样。她体重减轻了,头发变白了——引发了大量的欢迎赞美。这不是一个糟糕的时间。人来人往,她依旧交谈。礼仪惯例如何为一个人服务,那几乎是本能的呼唤和回应。她的新问候变得很好看,孩子。但时间也充满了恐慌和沮丧。她打电话给我说她无法呼吸。我停下了一切,跑了过去,但是当我们把她送到医生那里时,她给他看了她的脚。
最终,她不得不进入一个更有帮助的环境。她很喜欢这个地方,但讨厌他们的记忆程序——她不玩小游戏,她傲慢地宣称。她的医生建议她的比赛实际上可能太难了,她的拒绝是对衰落羞辱的更大反抗。我的母亲正在失势,没有任何记忆游戏可以阻止它。
我努力进行下一步——进入上锁的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病房。这似乎是一个失败。我一生都在反抗我母亲的控制欲。现在轮到我放手并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这就像重新学习做父母一样——用太极手引导,观察,轻轻推,后退,倾听,允许。就像养育孩子一样,情况从来没有稳定过;它总是在变成别的东西的路上。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尔玛很快就适应了病房,并以惊人的快乐参加了活动。
我们意想不到的第三幕继续展开。
我不想在上面涂上玫瑰色的光芒。有时她会变得如此愤怒和暴力,以至于工作人员不得不戴上护臂,以防我 87 岁的小母亲决定殴打或抓伤他们。把它贴上你的——!她会喊。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关系发展到了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的地步。当当地的 Sonny 和 Cher 乐队来访时,我注意到 Alma 在她的椅子上蹦蹦跳跳。我扶她站起来,我们一起跳舞,她在我怀里。在那之后,我开始把她带到她的房间,穿上一些 Sinatra 跳舞——如果她是她自己,这是她永远不会允许的。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踢球。她可以接住一个 Nerf 球然后把它扔回去,击打一个气球。我用蓬松的大刷子给她化妆,抚摸着她的眼睑和脸颊,她的手臂。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准备”。为了什么,谁在乎?
她喜欢音乐,现在一直在唱歌,儿时的歌曲、爵士歌曲、表演曲。她新的缺乏抑制让我感到难过,因为当她还在作画时,她无法与他人分享更多的自己。但她对自己的尊严有太多的感觉,不允许这样做。她要求一定程度的尊重。它是一尘不染的,和她仍在跳动的心脏一样深。然而在其他方面,她变得面目全非。作为男人世界里的职业女性,她对自己的性取向很谨慎。突然间,她是一个调情者!多么震惊,就像看到她十几岁的时候一样。我看着她和唐握手,他不知道谁是总统,但当被问到以 s 开头的单词时,他可以喊出一个拼字游戏。机缘巧合!塞伦盖蒂!
和许多控制欲强的人一样,她从不喜欢动物。但在一个感恩节,表妹的西施跳到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多么可爱的小狗啊,她沉思着,抚摸着它,让我无言以对。这让我想知道,什么是人?当我们不再记住我们的偏见和偏好,我们的意见时会发生什么?我们所认为的自己,我们所谓的性格,有多少只是拒绝,让我们远离可能会改善我们生活的经历的决定?
到那时,阿尔玛已经无法阅读了,但当我试图用图画书代替她沉重的大部头书时,她变得铁青。我的书呢?!她要求。我归还了它们,但留下了一些我知道会更合适的儿童读物。我读起来感觉很复杂 帽子里的猫 ,正是她和我父亲教我阅读的书。我让小鸭子进来 给小鸭让路 穿过威尔希尔大道前往麦克阿瑟公园,这是我们城市的地标。母亲和女儿在 萨尔的蓝莓 变成了她和我一起去优胜美地采摘蓝莓——这是我们唯一的家庭露营之旅中去过的地方。
看,那是你,我指着书中的黑发妈妈说,那是我,那个穿着工作服的邋遢的小女孩。还记得我们去优胜美地摘浆果的时候吗?她点点头,是的——她记得!出奇的深刻。在读那本书的过程中,我给了自己从未有过的童年,我们之间破碎的东西得到了治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阿尔玛的痴呆症让我们成为了我们从未成为的母女。
我给她做了一本关于她自己生活的书,拿了一个一英寸的环形活页夹和一些保护纸,扫描了她生命各个阶段的照片,放大了整页。 19 岁的阿尔玛·布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公寓里很漂亮。爸爸在他们的第一栋房子前面,有一棵细长的小树。上世纪50年代的夏威夷,他们两个,格外帅气。我女儿巧妙地拼贴了封面,并在封面上写了 ALMA。我妈妈很喜欢那本书。如果她情绪激动,工作人员可以把她带到她的房间,放一些古典音乐给她,让她立即平静下来。
最终她卧床不起,但她仍然有她的书和她的音乐。当她住院时,我带来了一个装有一副红色耳机的音箱,并在她的床上贴了一个大牌子:整天戴耳机。爵士站或古典音乐。一个躺在病床上不说话的疯子太容易被忽视了。我内心孤独的孩子明白:音乐是最好的伴侣。
我经常和她爬上床。她早就忘记了我是谁,但事实上我躺在她身边,给她读书——她知道我以某种方式属于她。我们一起看 帽子里的猫 或者她的书,直到她去世。我仍然记得我女儿的小手放在我脸上,拍着我的脸颊。我妈妈对我没有这样的记忆,但我现在有很多关于她的记忆,抚摸她,每天喂她两次,因为我有理由确信忙碌的治安官不会花 45 分钟给她喂一顿粉状的饭菜。她喜欢盐和黄油,我加了额外的——为什么不呢?
在以如此亲密的方式照顾她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在某种神秘的移情中成为了父母。事实证明,我是父母还是孩子、父母/孩子还是孩子/父母都没有多大关系。一直缺少的亲近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她死的时候,我正在给她念书 儿童诗歌花园 一首我以前从未读过的诗,告别农场,带着令人心碎的副歌:再见,再见,一切!我和她走到了最后,无法阻止任何事情发生,但就在那里。最后,存在就是一切。
关于作者
珍妮特·菲奇 (Janet Fitch) 是畅销书作家 把它涂黑 和 白夹竹桃 .她的下一部小说, 玛丽娜 M 的革命 ,现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