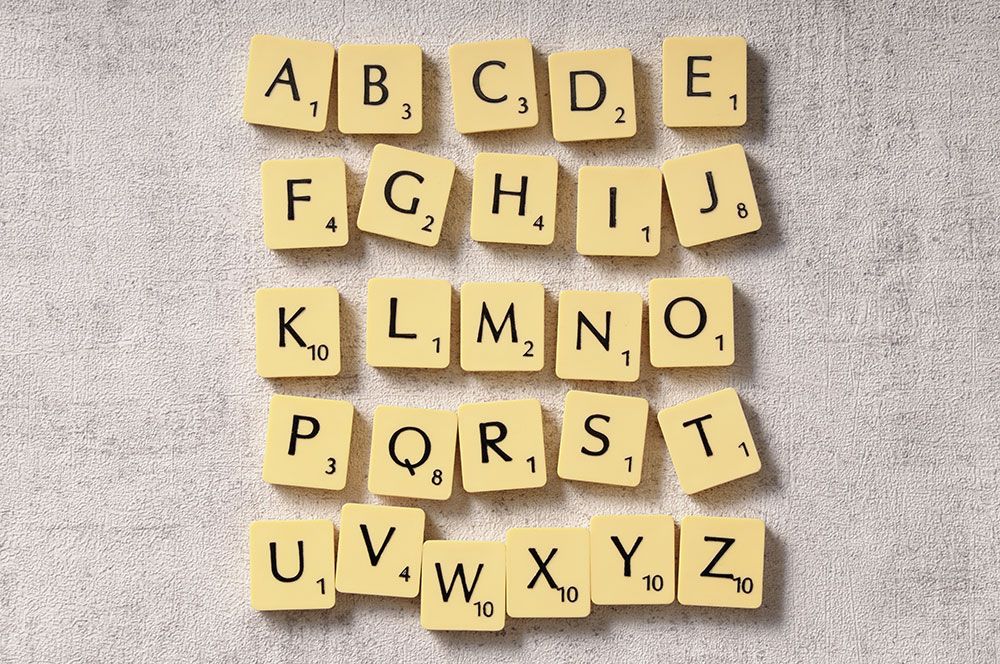1993 年,我的女儿——她 23 岁,是我四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去芝加哥读研究生,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当她经过宿舍外的垃圾箱时,听到几只刚出生的没有母亲的小猫悲伤的叫声,她一定感到陌生和迷失在一个新的城市,她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她捡起它们并将它们带到动物收容所,然后最终将其中一只带回家。他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男性,有一双小脚和一条粉红色的小舌头,当他哼着一首跳动的、低沉的情歌时,他的手指穿过她的手指——重复但强烈。她以一个老男友的名字给他起名叫乔伊。
她每隔几个小时就用吸管喂他一次,让他把脚缠在她的头发上。他长大了,到处都是白发。如果她轻拍她的胸口,他就会跳进她的怀里,把头靠在她的胸前,然后就睡了。芝加哥的冬天是残酷的——狂风呼啸,她房间的玻璃窗在密歇根湖的雨雪和狂风的影响下颤抖。乔伊玩弦乐。乔伊弄乱了她的文件。当她的男朋友来吃饭时,乔伊躺在餐桌的一侧。
几年后,她决定去波士顿的法学院,她带着乔伊长途跋涉,期间他对无聊和囚禁的抱怨被收音机里的音乐淹没了。在波士顿,他会在窗台上观看,直到她下课回来。他在别处度过了她生命中漫长的时光,她的生活没有他。然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男朋友走了,她搬回了家乡纽约市,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律师,尤其是年轻的律师,一大早就离开,深夜回家——所以乔伊变成了一只悲伤的猫。他的皮毛乱七八糟。他的眼睛眨得太频繁了。他被抚养长大,期望得到安慰和人性的手放在他的头上。
我带他和我一起住。当我丈夫上床时,看到乔伊蜷缩在我身边,他会说,嘿,猫,那是我的女士。下床!乔伊会跳下来,片刻之后他会从另一边上来,躺在我的枕头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们的呼吸混杂在一起。我会从他的呼吸中闻到猫粮的味道,他会闻到我喝的咖啡、我吃的香料、我每天涂的肥皂和洗发水、汗水和粉末的味道。做梦时,他的胡须有时会在睡梦中颤抖。
就这样了。我女儿结婚了,并没有要求乔伊回来(尽管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把他给她)。我的黑色裤子上覆盖着他的白色皮毛。我的黑色毛衣经常急需清洗。当朋友来吃饭时,我会说,不要把你的外套放在床上,因为乔伊会依偎在他们中间。厚厚的白发束嵌入纤维中,缠绕在外套纽扣上。如果我忘记给沙发或椅子吸尘(而且我经常忘记),我的客人会站起来,白头发盖住他们的屁股。这很尴尬。
当我有对猫过敏的客人时,我会把乔伊锁在浴室里,直到他们离开。我讨厌这样做;他是我真正的影子,我的四足自我,我的朋友——更不用说我亲爱的女儿的快乐提醒,以及她从垃圾箱里救出一只小而无助的小猫的行为。
2005 年,我丈夫去世时,乔伊占据了他一半的床位。如果我一大早醒来,我会抚摸他的肚子,直到他高兴地发出咕噜声,然后再继续睡觉。或者乔伊会用他的砂纸舌头舔我的脸。或者当他用前爪揉毯子时,我会躲在被子里。
一天晚上,我惊醒了。乔伊在尖叫——一声高吼,一种包含抽泣的尖叫,一种女妖的声音,一种可怕的声音说 痛,痛,痛 .
我跳起来,发现他压在厨柜的白色门上。他的背高高拱起,用瘫痪的腿拖着自己向前走。我看了看时钟。现在是凌晨 2 点 30 分。好吧,我想,我会在早上带他去看兽医。
我试着回去睡觉。但即使我把枕头放在头上,我也能听到他的嚎叫。我找到了一家通宵紧急动物医院,距离大约 40 个街区。我穿着。我把乔伊放在他的手提箱里。他的皮毛湿了。他的眼睛很狂野。他的鼻子滴着液体。当我把他推进笼子里时,他试图咬我。
我下了电梯,走到拐角处,等待着。终于来了一辆出租车——那辆孤独的出租车停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在艰难的时间里,我什至看不到伴随着失眠症患者的电视屏幕的蓝色模糊。
在动物医院,墙壁太亮了,太刺眼了。一位昏昏欲睡的接待员守卫着办公桌。乔伊呜咽了一声,然后发出了可怕的哭声。几分钟后,一位兽医过来带走了乔伊。医院里的灯光让我想起了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一幅画:空气中徘徊着某种超越空虚的东西。没有其他人从医院的门进来。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您不会认为自己可以独自面对灾难。
最后兽医让我进入检查室。她年轻而温柔,她的绿色磨砂对于她的小身材来说似乎太大了。她说乔伊有动脉瘤。这是行不通的,他们应该让他立即睡觉,以免他再受苦。他 14 岁。
兽医说,那是一种美好的猫生活。她给了乔伊镇静剂,他瘫软地躺在我的怀里。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失去了完整性——一条腿、一条尾巴、一只耳朵都奇怪地弯曲着。他粉红色的小舌头从他倾斜的嘴里伸出来舔我的手指。
我给你一点时间说再见,她说。
就去做吧,我回答说。
她给他注射了他臀部后面的肌肉,我等着。他不动了,然后更不动了,当他最后一根白发粘在我的毛衣上时,他的胸口停止了起伏,他死了。
我付了帐单。我穿上外套,走出医院的旋转门。我想知道:自从我听到他的第一声哭泣以来,已经过了多久——一个小时,也许两三个小时?
东方的天空越来越亮。一辆垃圾车呼啸而过。角落里的小餐馆里煮的咖啡。我路过的时候闻到了。我没有被悲伤所压倒;我一直都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当我走在大街上时,一种平静的感觉,就像一条温暖的披肩,包裹着我。乔伊这个曾经像垃圾一样被扔掉的老猫,首先是因为我女儿救了他,然后因为我喂了他,抚摸他,忍受了他的脱落,换了他的垃圾,我工作的时候让他坐在我的桌子上。当他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只老鼠的礼物时,我并不介意;我称赞他作为猎人的狡猾。我们同住一个家,他是个好伙伴——这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小事。
是的,我必须适应他不在的情况,当我打开门时,当我坐在沙发上时,当我在床上翻身时,我会想念他。但我明白他花了时间,我们彼此相处得很好。在人兽飞鸟的浩瀚宇宙中,我们都只是一粒尘埃,短暂的相聚。乔伊过着体面的生活,也过着体面的死。
那天下午,我准备去布鲁克林和我的女儿共进午餐,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乔伊一直是她做母亲的练习。他是我最后的喘息吗?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冬天寒冷的空气。我想知道报纸是不是已经送到了,还是太早了。然后我考虑养一只小猫。我回到家,查看了我的电子邮件。我应该养一只橙色的小猫吗?在停下来之前,我又一次想了想。也许这是另一个时间的想法。
安妮·罗菲 是最近一本回忆录的作者 艺术与疯狂 ( 亚马逊网站 )。她还写了 18 本书,包括 结语 , 上沙盒 , 和 卓有成效 .她住在纽约市。